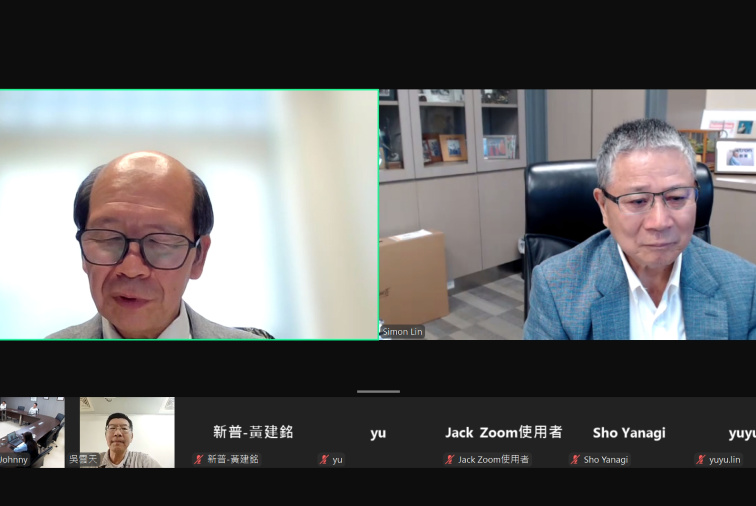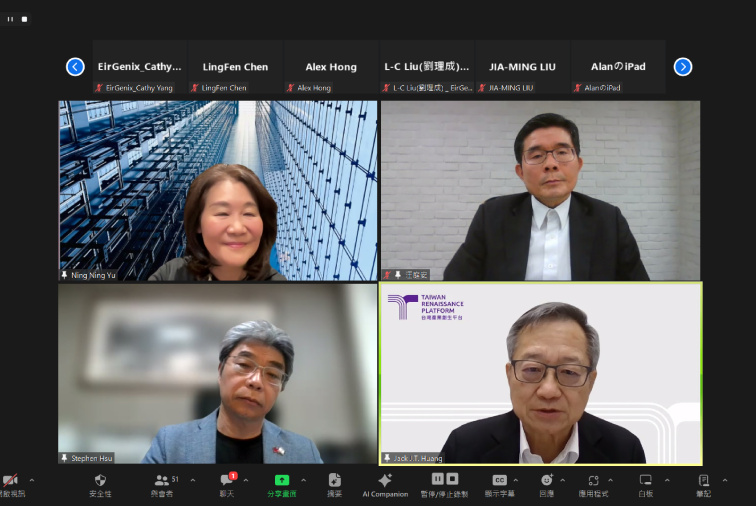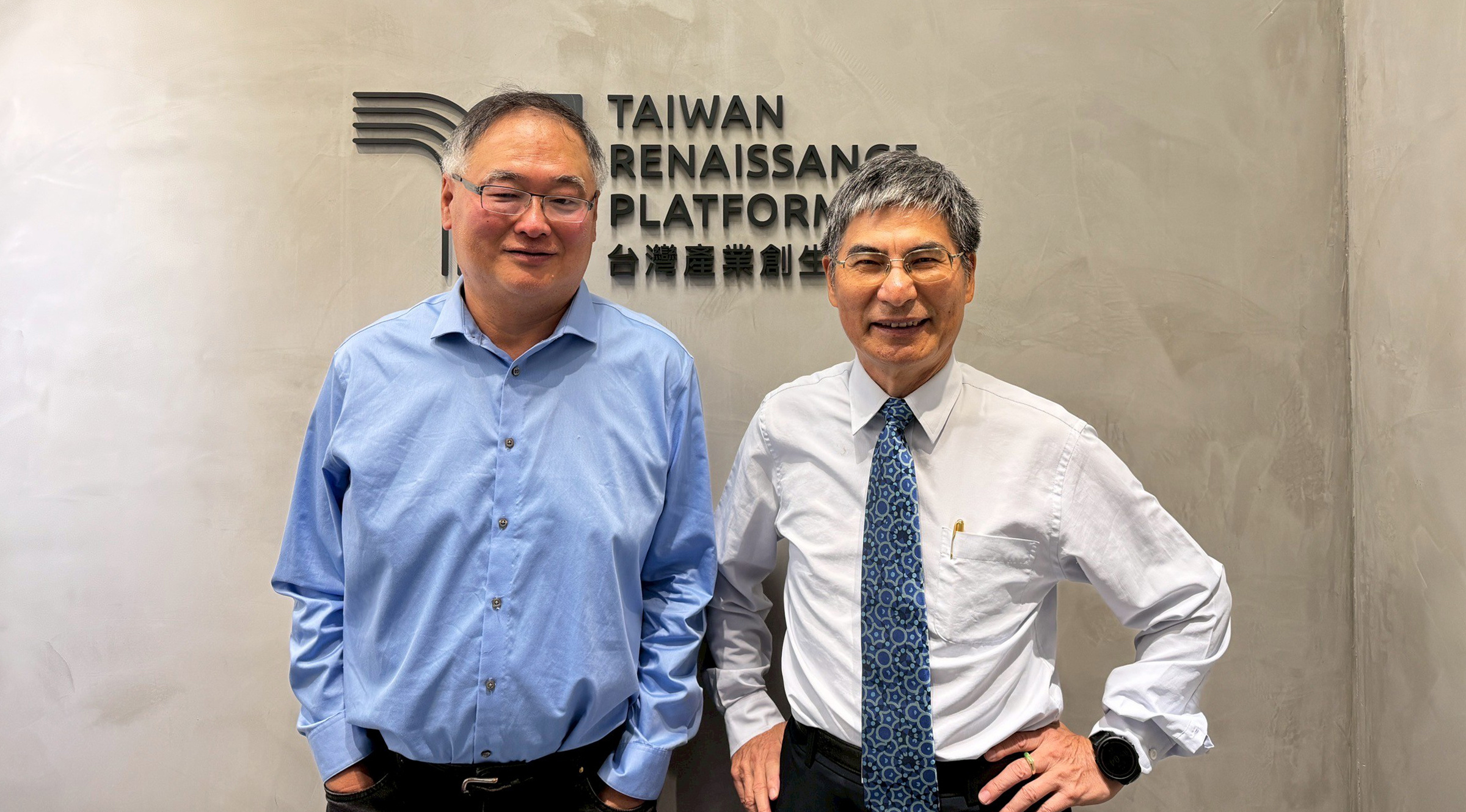
「台灣正面臨一個產業轉型的時代,我們該如何善用今天台灣的能量與熱情;尤其是20、30歲世代的熱情,讓20年後的台灣,能到達真正符合我們期待的地方?」這是8月「Future Calls-預見未來」的線上講座中,擔任主講者的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謝長泰語重心長的一段話。
本次線上閉門論壇,台灣產業創生平台邀請到謝長泰,以「工研院的下一步:在升級與轉型中重塑功能與定位」為題進行線上演講,並由前科技部部長陳良基主持。

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發展與成長的謝長泰,2023年,他在《天下雜誌》的專欄中,以〈台灣該告別工研院嗎?〉為題指出,台灣如果沒有工研院,恐怕不會出現半導體業,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,「台灣需要一個能夠應對當今面臨科技挑戰的新機構。當世界發生變化時,機構都應該變化。」
本次會中,謝長泰探討50年前台灣經濟百廢待興,是工研院引進關鍵技術,為台灣播下「晶片」種子;如今,工研院在完成上一個世紀的階段性任務後,未來20年,該扮演怎樣的角色,協助台灣新一代去實現他們的夢想。主持人陳良基也不斷提醒,若我們思考的不是「明天」而是「後天」,就必須要將眼光放得更長遠。

本次講座,線上報名相當踴躍,顯見大家對台灣未來產業升級發展,有相當大的期待。以下為內容摘要整理。
政策的角色不在於替市場選擇「贏家」,而是提供必要的制度與資源
謝長泰開宗明義就先分享兩部最近他所看過的台灣紀錄片,第一部是關於台灣半導體產業起源的《造山者-世紀的賭注》(Chip Odyssey),第二部紀錄片是《看不見的國家》(Invisible Nation),兩部紀錄片講述的都是台灣精神的本質。
《造山者》這部紀錄片聚焦一小群在1970、1980年代初於工研院(ITRI)工作的人的故事。謝長泰稱這群被送去RCA學習半導體技術的人為「RCA幫」。
他表示,這個故事所傳達的訊息、以及它對台灣歷史與未來的啟示,其實核心模型是「該怎麼做」。它呈現的模式是,台灣人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努力。我們需要這兩個群體努力工作;首先是科學家與工程師努力先去習得技術與方法,接著工人再努力去應用這些技術。依此推演,影片隱含的訊息就是,未來產業創新的成功關鍵在於找到正確的領域,不論是生技、人工智慧,或其他,然後再套用這個模式。
但仔細想想,這部片少了幾個面向。有一個有趣的片段,是傳奇人物史欽泰開玩笑說,RCA可能把他們當成間諜。這就引出一個問題,今天這個世界上,還有哪家公司會讓你花錢買技術,並允許你派工程師來學所有東西?我們還能在哪裡獲得這樣的知識?謝長泰認為,RCA 的案例其實是一個歷史巧合,在今天幾乎不可能再發生的事。
至於《看不見的國家》講的是有想法的人,投入社會運動,並改變世界。但謝長泰認為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故事,今日台灣真正的活力與熱情在哪裡。現在有很多人有想法,想要有所作為,只是這些努力可能面臨更多挑戰。所以他想問的是:「我們該如何善用今天台灣的能量與熱情,尤其是20、30歲世代的熱情,讓20年後的台灣,能到達真正符合我們期待的地方?」
他指出,台灣半導體之所以成功,1970年代的工研院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,但部分關鍵在於工研院懂得「何時應該適時放手」。他們能辨識出哪些方向不可行,並願意及時停止,避免繼續耗費資源。正如前工研院院長史欽泰在《從邊緣到核心:台灣半導體如何成為世界的心臟》一書中所提到,故事的重點不僅在於成功,更在於失敗案例帶來的啟示。
因此,謝長泰認為,最理想的模式,應該是讓人類的創造力能自由發揮,並承認優秀的創意可能來自任何角落。政策的角色不在於替市場選擇「贏家」,而是提供必要的制度與資源,使創意得以被驗證。
台灣面臨兩大創新挑戰:金融體系的不足與職場文化的限制
謝長泰進一步指出,政府更務實的做法應該是建立一個環境,讓創新能直接接受市場檢驗。支撐這一點的基礎設施,其實就是一些最基本的要素:土地、空間與資本的取得。但目前台灣面臨兩大挑戰:一是金融體系的不足,這屬於政策面向;二是職場文化的限制,深植於社會與商業文化之中。
他以資本市場為例,台灣在金融改革時錯失了一個關鍵契機。今日的銀行體系缺乏競爭力,大量資金被鎖定於外匯存底與保險業,無法有效流通以支持創業生態。台灣缺乏能夠支撐創業發展的金融基礎設施。
此外,文化因素亦不可忽視。台灣的「老闆文化」與僵化的職場氛圍,使員工難以獲得試錯與創新的機會。在一個組織中若沒有發言權,僅能依循命令行事,那麼「我有個想法,讓我試試看」的本能,不是從未被培養,就是最終被磨滅。
正如紀錄片《造山者》所暗示,RCA工程師知道如何執行,但若有人有更具突破性的想法,制度是否允許這些構想浮現,才是真正需要深思的問題。換句話說,如果制度只獎勵服從,那麼我們便可能錯失來自意料之外的重要創新。
他再補充,技術只是故事的一部分,更大的一部分是組織能力——如何進行設計、如何組織員工、如何有效擴張、如何激勵與管理人才。這些組織能力往往是偉大企業的核心,甚至有時比技術本身更為關鍵。
因此,謝長泰建議,我們需要以更全面的視角來理解企業成功的本質,並承認優秀的創意可能源自任何地方,不必限定於實驗室。舉例而言,「珍珠奶茶」正是一個台灣錯失的國際化契機。台灣本有潛力將其打造為「珍奶界的星巴克」,卻未能充分發揮。
主持人陳良基回應說,1976年,台灣派遣RCA團隊赴美受訓。在那之前,台灣已經有一些電子公司,像是華泰電子、飛利浦等從事封裝與組裝工作,那就是台灣電子產業的起點。也正是在那個時候,電機工程迅速成為大學中最熱門的科系之一。
今天的年輕世代也在問類似的問題:我們的下一個前沿在哪裡?如果一個產業已經由上一代建立起來,年輕世代自然會覺得這是既有的、已經被「擁有」的領域,因此他們會尋找新的想法與新的機會。
陳良基認為,這正是謝長泰所提到的「政府選擇」與「企業選擇」的重要之處。不過,政府要為產業做出一個明確唯一的選擇是非常困難的。相反地,政府應該要嘗試、實驗,並在多個方向投入。它可以把預算平均分配在不同的領域,提供平等的初始支持,然後觀察哪些領域最能吸引人才與展現能力;一旦某個領域顯示出潛力,政府就能進一步建構基礎設施來支持它。
至於企業的選擇在於如何將技術與可行的商業模式結合。當技術走到可以被商業化的階段時,本身的技術通常只是挑戰的一小部分。一旦技術被理解並探索完成,真正的任務就是如何把它整合成顧客願意購買的有用產品。在這個階段,企業必須把技術與正確的商業模式結合起來。政府選擇,很難做到;企業選擇,則是企業轉型的使命之一。
今天的台灣,產業依然多元,但仍在資訊科技領域扮演關鍵角色。如果台灣能以自身在資訊科技的優勢為基礎,延伸到更多不同的商業領域,辨識出哪些產業重要且具潛力,將是至關重要,且可能會指引我們走向台灣未來的「使命產業」。
如果你是李國鼎,此刻你會怎麼布局台灣未來
會中交流時,主持人陳良基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反問謝長泰;「如果你是李國鼎,此刻你會怎麼做?其實,這正是我十年前擔任科技部長時所面對的壓力之一。」
謝長泰的回答是,他會從一些小而實際的事情開始。例如,他現在關注台灣的一個問題就是保險產業。他相信這個市場即將迎來一場金融爆炸,最大的一個隱憂是,如果新台幣繼續升值會怎麼樣?若它持續升值,整個體系可能會很快瓦解。監管單位必須採取行動,否則將會出現嚴重的金融災難。
另一方面,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,可以藉此進行結構重整,讓資金不再只是流入美國國債。現在有大量的資金停留在美國國債裡,但同時,很多專案卻得不到所需的資金,他認為非常浪費,把錢放在幾乎沒有實質報酬的美國國債裡,而真正有價值的專案卻無法獲得資助。
所以他的問題是:「我們該如何進行結構重整?我們應該討論中央銀行的角色是否需要調整。央行真的有必要持有那麼龐大的外匯存底嗎?這些資金能不能被用在更好的地方?」這同時是一場潛在的危機,但也是一個巨大的機會。
主持人陳良基回應,他也認為這是台灣的潛力之一。台灣有許多人才投入半導體與健康系統。如果這些人才能夠累積更多創業經驗,嘗試將系統模組化,並結合產業發展,那麼我們就有機會讓這個願景成真。
這也是為什麼,當他從工研院卸任後,創立了一個名為「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健康產業發展協會(TAIDHA)」的機構。這代表了台灣潛力的一部分,我們的技術優勢能夠延伸到具有特殊需求的領域。如果能夠透過金融或保險資源來支持並解鎖這個產業,台灣就有可能在這個領域中取得主導地位,因為所需的關鍵技術,大部分我們其實已經擁有了。
上騰生技顧問公司董事長張鴻仁也回應指出,政府有很多規範,阻止了產業在保險醫療或數位轉型上的推進。很多數位轉型計畫完全沒有進展。當我們推崇新南向政策,想把產品推到其他國家時,事實上,我們連在自己的市場都推不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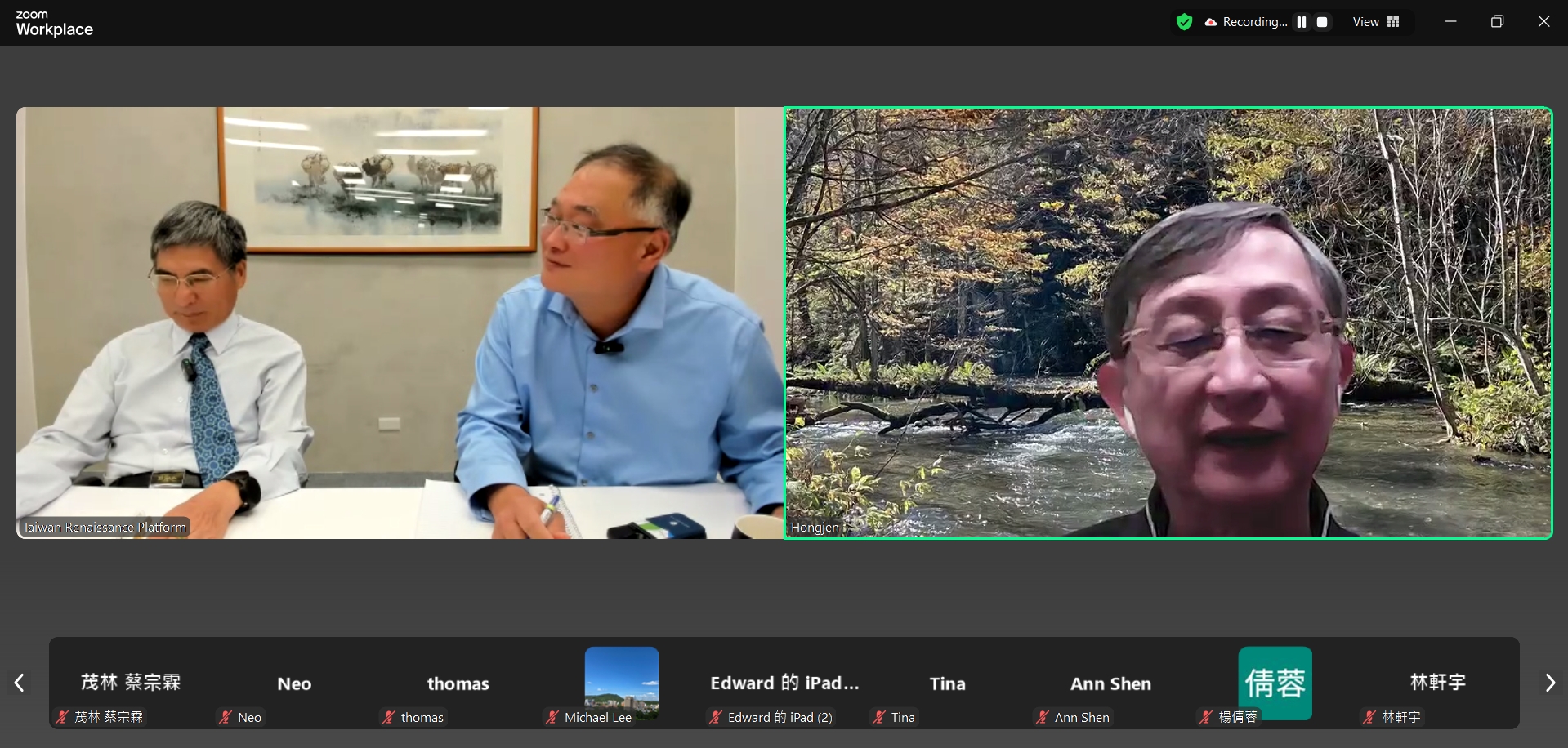
他曾在「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」(BTC)裡提過,現在台大開發的系統,長庚不用;長庚開發的系統,榮總不用。台灣的醫院都是各自為政,每家醫院都有自己的系統。雖然我們有一張健保卡,確實很方便,但這個專案是30年前啟動的;當時是很高尚的理想,但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過時的系統。
台灣有很多年輕版的「黃仁勳」,他們需要有機會茁壯成長
謝長泰回顧台積電的起點,當時完全是靠政府資金支持,但這樣的模式並不能被普遍化,我們需要一個更系統性的方法來推動,而現在這樣的系統仍未建立。
他觀察,現在台灣有很多年輕版的「黃仁勳」,許多二、三十歲的年輕人和黃仁勳很相似。他認為我們要做的就是,不要成為他們在道路上的障礙,去阻擋他們;相反地,要讓他們能夠更容易去探索自己想做的事,並且真正去實踐。
換句話說,應該讓台灣的年輕人及整個生態系統,自己去做出選擇,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。政府的角色,應該是確保這些人有機會茁壯成長。
謝長泰指出,人並不總是只被金錢所驅動。在晶片產業中,真正驅動人們的往往是其他東西。例如,RCA幫那一群人幾乎有一種信念、一種堅定的信仰,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能改變世界。這種動力遠遠超越金錢;像是史欽泰這樣的人,他從來沒有加入任何一家大公司。當人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懷有一種信念,甚至接近宗教般的執著時,真正偉大的成就才會誕生。
他分享幾年前,他去饒河夜市一個米其林小吃攤的經驗。試想,哪裡還能用120元新台幣就吃到米其林認證的美食?米其林的背書代表這家攤位,連同其他大約50家,被認為是全球最頂尖的餐飲之一。他排隊一個小時,攤子只是一位母親與女兒經營,最後等不下去,只能放棄。
他舉這個例子是要告訴大家,這是一個有明顯全球需求的台灣產品,但問題在於,小吃攤並沒有一套組織能力來滿足需求。就好比台積電能造出世界最好的晶片,大家都想要,但如果要買一顆晶片,必須親自到新竹,且他們一天只造得出一顆,那麼台積電就只是一個夜市小攤。即便擁有世界級的產品,若缺乏能夠規模化的組織,最終仍無法產生真正的產業價值。
台灣到處都有類似的例子。可是,像這樣的夜市小攤,從未被台灣的產業規劃者納入考量。因此,謝長泰認為,大家需要轉變思維,更開放去接納多元來源的創意,並聚焦於如何協助這些人擴張規模,這才是真正的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