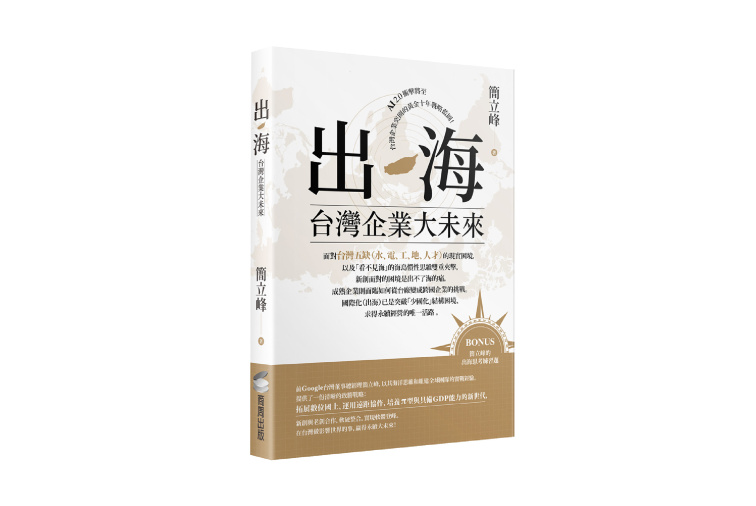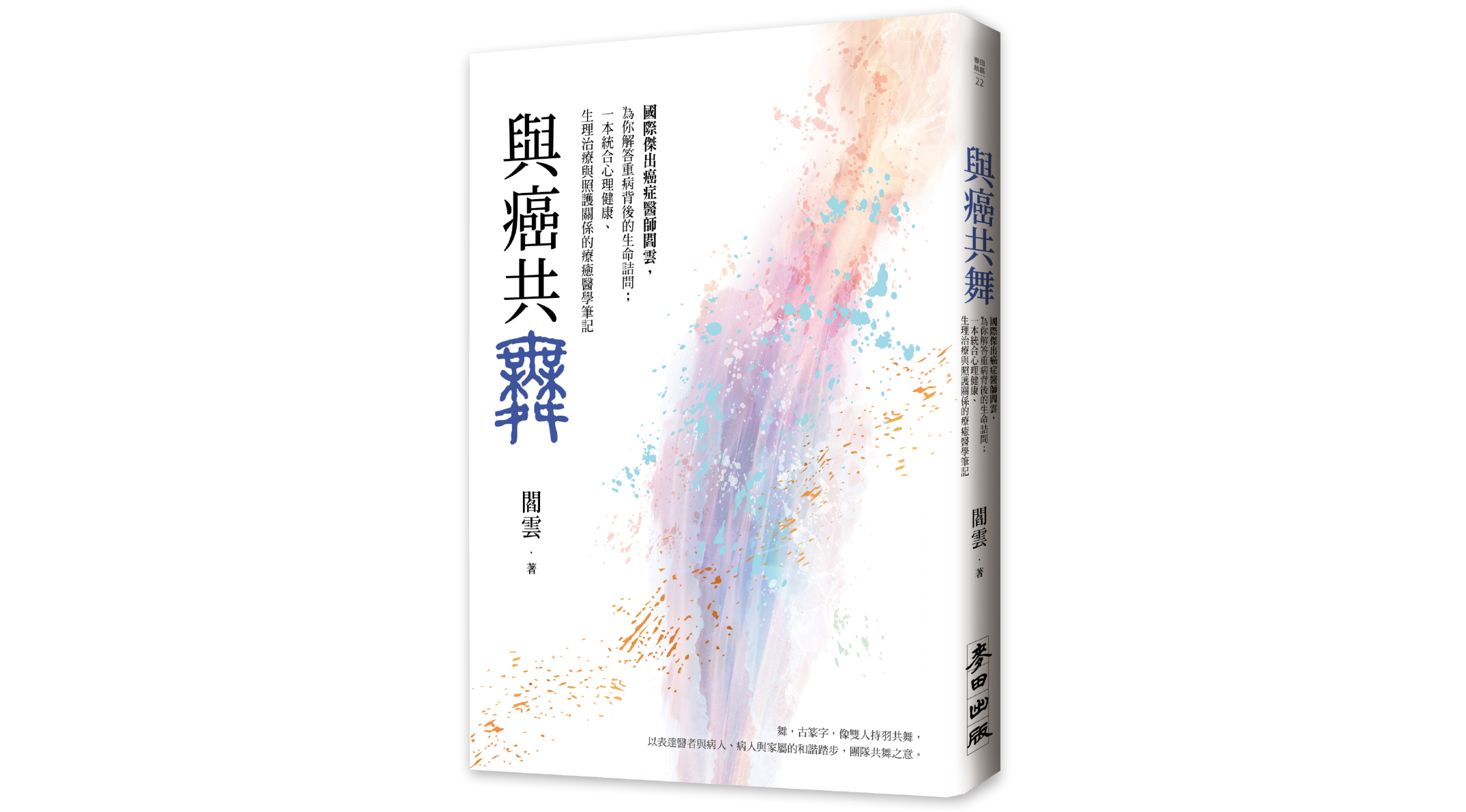
根據衛福部統計,癌症(惡性腫瘤)自1982年起,已經連續43年居國人十大死因榜首,當代人面對癌症與生死議題,究竟應抱持何種態度?國際知名癌症醫師與研究專家閻雲,將醫療現場第一手故事與資訊彙整成《與癌共舞》這本書,希望提供正確且健康的指引。
閻雲曾任臺北醫學大學校長、美國希望城癌症中心副院長,是國際知名的癌症研究專家,在血液、腫瘤、骨髓移植等領域鑽研極深,2016年當選美國國家發明家學院院士及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士,2025年獲得美國臨床腫瘤學會(ASCO)授予的FASCO終身會士殊榮。
他在《與癌共舞》這本書中,結合臨床故事、醫病關係互動、患者與家屬的各式提問與盲點,涵蓋癌症預防與治療、家庭遺傳、心理建設、醫藥發展歷程等內容,並涉及跨越生死界線,擁抱家庭與愛等議題,不只教讀者抗癌,更提點如何與癌共存的心態與知識,堪稱一本統合心理健康、生理治療與照護關係的療癒筆記。
閻雲不只看重病體,還重視醫心,不僅看重專業,還重視人文素養,在這本橫跨醫學與人文的書籍中,他從自身經歷過的病患汲取例子,探討醫病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——不僅是醫者與病人,還包括醫者與病人家屬、病人與家屬,甚至是病人周遭的親人與朋友們,對於重病背後的生命詰問,以及人際間的關係與疾病挑戰,提供了難得的觀察與省思。
以下摘自本書第一章:
每天都是情人節
我想為這個故事,寫下一個題目:「每天都是情人節」。
這是一位年少時跟著鑽探海上石油的工程師父親,在汶萊長大的女性。她天生非常有國際觀,活潑、熱愛運動,或也可以簡述:婚姻生活美滿,先生全力衝刺事業,他們有兒有女,非常幸福。當她六十歲左右,右側乳房發現異狀,由於是早期發現,手術即可。大約一年之後,左側又發現了比較激烈的癌細胞,於是開始常規的化學治療。且由於她的腫瘤檢測出HER2 gene positive(惡性程度高的乳癌基因陽性),因此,也投以藥物Herceptin(賀癌平,一種標靶單株抗體)。治療之初效果很好,然而,不過一年,又再復發了。這次復發,便發現腫瘤指數不僅增加,更轉移至骨頭,只得接受局部放射治療。
如此起起伏伏長達四年的時間,基本上所有一般人了解的、想得到的治療都做過了。但是,就在局部放射治療之後,腫瘤仍是轉移至腦部,此外轉移至骨頭的癌細胞,也影響她的行走,有時需要輪椅或柺杖,開車也成為困難的事。就在此時,與她年紀相仿,事業仍在巔峰的先生,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。有一天,先生回到家時告訴太太:「我要退休了!」太太不相信,因為她的先生是一個工作狂,一生忙忙碌碌只專注在工作上,這樣的人,怎麼可能此刻退休、閒在家中?
先生再次告訴她:「不,從此刻起,我的職業只有一個了,就是照顧妳。」於是,從這一天開始,每次她去就醫、放射治療,都是先生開車,門診結束,她的先生便會帶著她,倘若她的身體狀況尚可,他會尋覓一間頗佳的餐館一起用餐。若她的胃口不佳、沒有食欲,他會準備一些可以刺激食慾的食物,比如帶有香氣的、微帶些醋味的……但是,又不能太過刺激,因為太酸的食物,會使她的口腔黏膜酸痛;有時,因藥物作用,口腔過於乾燥苦澀,則需要濕潤且緩慢地用餐。先生便很有耐心地陪伴她,兩人慢慢地吃一頓很長的中餐,然後帶她回家。當她倦了累了睡覺了,他再去做自己一樣熱愛的工作,將專業文章慢慢整理、慢慢發表,其中有許多發表在非常好的期刊,他一點也沒有放棄或閒置了。
前不久,情人節將至,我們兩家人約定共度晚餐。聊著聊著,大家笑問:「今天是情人節,Matt(先生名)有沒有對妳表示什麼呢?」太太說:「不需要表示了!我現在太快樂了,每天都是情人節!誰會天天開車送我去醫院呢?有誰會天天請我吃飯?所以,對我來說天天都是情人節。」
這對夫妻讓我感動的是,當丈夫意識到妻子所剩時間未必太多時,他決定要把自己的時間留下來,陪伴她。放棄美國教授的終身職,早晨起來,他們一起去爬山,當妻子的行動力越來越不靈敏時,他扶著她走。身為病患,有數之不盡的各種醫療,今日驗血,明日注射,後天要放射治療等。先生就是開車帶著她、陪伴著她。
現今社會中,我們可能更慣常聽到這個離婚、那個家庭破裂。然而,在醫療現場,真實人生,美好的事情仍每天發生。
另一位本身非常有能力、很有成就的老太太,患病時,已經九十四歲了。由於她的Lung cancer(肺癌)是非小細胞肺腺癌,一開始可以手術切除,非常順利。但是很不幸地,約也是過了一年多吧,追蹤掃描時,便發現從前切除處有黑點,甚至於淋巴結處,發現陽性反應,顯然已經變成比較aggressive凶猛、具侵略性的腫瘤了。非常幸運地,透過基因配對檢測出,有相應的標靶藥物可以使用。當她接受治療後,針對抑制腫瘤細胞,效果的確很好;可是也出現關節痛、皮膚乾燥等標靶常見的副作用。
過程中,她也十分忍耐,但是情況越來越辛苦時,我問她:「需要找人照顧妳嗎?」她說:「不要,因爲我還要照顧我家的先生。」原來,這位九十四歲的老太太,還要照顧九十九歲的先生。她斬釘截鐵地說:「我絕對不能死在他的前面,他有一身的慢性病,糖尿、高血壓、心臟衰竭,還要帶著尿袋、導管,這些都需要常常更換……這些我都學會了,我都可以幫他;他不喜歡別人碰他,只有我可以照顧他。」我又問她:「那麼,妳的疼痛,怎麼辦呢?」她說:「那有什麼?我先生叫得比我凶,我都忘了我的痛了。」
你看,年齡本身其實是相對的,九十四歲,我們覺得已經很高齡,但是她還強烈希望照顧先生,這當中沒有任何怨懟與牢騷。對她而言,必須活!她活下來的意義,早已不僅僅為了Anti-cancer(抗癌)。她活下來的意義是「我要照顧他」。
接下來,也是一位女性的故事。她是我在耶魯大學的祕書,當年自由自在,標榜自己不需婚姻,也不會結婚。但有一天,我聽到消息,說她要結婚了;並且,對象是我們曾經治療過的病患的先生。原來,在病患逝世之後,這位先生前來感謝醫院的多方照顧,祕書不斷安慰他,並且後續開始通信,竟使他們有了共度餘生的念頭。那時,男方六十歲,這位號稱終生不婚的女性四十五歲。
再聽到他們的消息時,祕書已經將近八十歲了,先生九十五歲。由於先生退休於某家經營十分成功的企業,能終其一生享有非常寬渥的待遇,然而,因為二婚的緣故,在老先生需要耗費龐大醫藥費的情況時,前妻的幾位子女,也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。他罹患的是前列腺癌,許多前列腺癌經過治療便可痊癒。但是他反覆復發,藥效亦不見明顯,於是疼痛不斷,更兼要穿尿布,也需要放射治療等等。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,時好時壞,時壞時好,平素就是妻子一人照顧他。但是,即使是他這般經濟寬裕的處境,醫療時間一旦拖得長了,保險金無法支付時,只能動用自己的存款。此時,爭端便出現。他的子女冷言冷語地說:「你要把這些錢花完了,你也救不了你的命,又何必呢?你都已經九十五了,對不對?放棄治療吧。放棄治療吧,這樣子不是大家都好嗎?」並且說:「繼母照顧你延續生命,是讓你痛苦,只是爲了顯示她自己的身分。」
如此一來,象徵平安喜樂的「聖誕節」,變成一個令她恐懼的節日。倘若邀請孩子們一起過節,便會爭吵不休,倘不邀請,像剝奪了他們相聚的時光!
某一年,也是靠近聖誕節時,我的祕書發現她腳上有一個黑痣。通常,位在腳底下的一些黑痣,一開始沒事,後來若有出血,又疼痛,甚至變大,大概就知道不妙了。因爲她畢竟曾在醫療單位做事,熟悉狀況。就醫檢查後發現:是一個黑色素細胞瘤,而此類腫瘤越偏周邊越要儘速手術,它才不會轉移他處。倘若再晚處理,接著就可能是淋巴結,那便進入晚期了,所以她接受了部分amputation(截肢)手術。她十分努力復健,這期間,她亦未停止照顧先生。她說:「我一定要讓他的兒女知道,我是真心照顧他,我們是有真愛的。」
身為病患,也身為照顧者,需要非常大的勇氣與毅力。我們站立與行走,所依靠的正是腳拇趾的平衡。但是她的黑色素瘤正長在腳拇趾下,因此,她被切除的就是一個腳拇趾、一個腳趾,還有一部分的腳,走路需重新訓練。但她如此堅強,她說:「我一定要站起來。我一定要繼續,我要證明給他的孩子看。我不是爲了他的錢。」她不只是他的妻子,還是他的護士。她說:「我現在是nurse but not purse。」[美國諺語,指她不是為了他的錢包(purse),而是提供服務的護理師(nurse)]
由此,我也回憶起另一個真實的故事。
這位病患,現在已經五十歲了。他出生後不到一歲時便得了血癌。當時他們住在紐約,他的母親帶他去了田納西的St. Jude Children's Hospital。這是研究兒童疾病的專門醫院,主要治療與研究兒童重大疾病,特別是白血病和其他癌症。因爲那裡是治療小兒血癌非常好的地方,母親帶著他在那裡住了整整一年,照顧他,陪伴他。後來他的血癌便治癒了,終生,直到現在都沒有復發過。但是,成長過程當中,他對自己的身體一直不太有信心,他容易疲倦,也比一般人容易貧血,甚至多病。平常的我們,說一句「多病」,簡單得很,然而,對母親而言,他的每一次感冒、發燒,都是視如一級戰區來處理。因爲她心中擔心的都是:他的血癌會不會回來。
這位病患有一個哥哥,哥哥大他三歲。他的哥哥就經常感到不平;因爲他小的時候哥哥年紀亦不大,但是媽媽總用全部的精神力氣照顧弟弟,所以哥哥與他的感情便不好。一直到年紀較大以後,才算比較可以諒解。但是兄弟之間一直存在隔閡,尤其,哥哥身體非常強壯,如運動員那樣子的體魄;弟弟卻經常是站在運動場外面,沒有辦法參與任何的球賽,只能看著哥哥,為哥哥加油。而他的媽媽卻總是經常問他:「你今天覺得怎麼樣?」這樣子到了他五十歲。他的媽媽也在此時罹患了失智症,一開始是偶爾忘了他的名字,漸漸地,開始認不出他,甚至叫錯。他的哥哥就告訴他:「你看,她再怎麼樣叫錯名字,卻連叫我的名字都沒有。」這個衝突就這樣持續著。母親後來不僅是失智,並且會失蹤不見。曾經有過兩次失蹤的經歷,所幸都找回來了。家人於是決定將她送往護理之家。他每天下班以後一定去看她,陪伴媽媽直到護理之家關門為止。
他終生未婚,因爲他不敢結婚。第一個他可能不能生育,這是很常見的,特別是早年血癌的治療,大部分都會遺留不孕的後遺症,今日醫療當然大不相同了,也許會透過凍卵預先防範。但他因為幼時血癌的經歷,終生沒有想過結婚,也沒有交過女朋友,就如此全心照顧母親的晚年。他的母親今天仍安在,他也還在。有時候,護理之家的護理師會問他:「她為什麼一直在說田納西的事,你們是田納西人嗎?」他的媽媽越來越失智了,但是當腦子越是退化以後,記得的卻是越早的事情。他告訴護理師,母親曾帶著罹患血癌的他,在田納西住了一整年,她雖然退化了,卻仍記得田納西⋯⋯
這裡所記下的、描述的,每一個都是活著的人,真實的人生。癌症的宣告每每如似天崩地裂,然而,山河震動之後,仍可以選擇不同的態度與重新生活的方式。
(本文摘自《與癌共舞》,由麥田出版授權刊載)